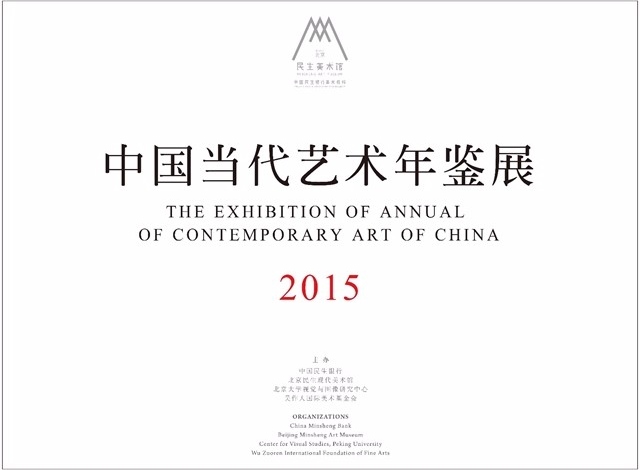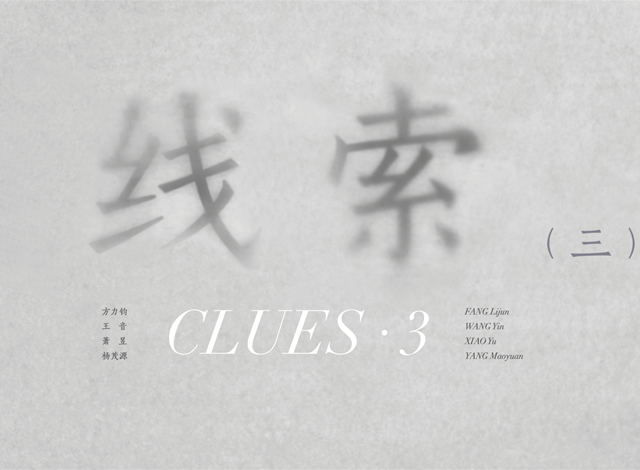前言
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
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更是艺术之路。
非只一条的丝绸之路繁忙异常。西来东往中,既有陆上、海上之别,又有南线、中线、北线之分。它们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活跃度,各领一时风骚。“艺术”以不同方式在丝路沿途传播,生长演变,并碰撞出火花。多种文化互鉴交流,多种文明融合汇通。造像、壁画、书法等这些我们今天视为艺术的载体,起初只是寺院或墓葬装饰、法律文书。历经千年
雨打风吹,它们的原有功能如今大多不复存在,只留下形式之美,以文物与艺术之名供后人叹赏。
“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借由“序篇”“大地”“人间”“天空”“艺术恒久”五个篇章,呈现陆上丝绸之路东段,从洛阳、长安到新疆这一区域丰沛的艺术样貌。500余组件展品,跨越4000年,涵盖绘画、雕塑、造像、器物、声音、影像、多媒体等多个门类,共同营造出立体的多维场域――丝路艺术的多样,坚韧,活力。它们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悄然改换着妆容,不断再生出新面貌。不仅如此,它们历久弥新,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们以启发。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如今创造丝绸之路物品与艺术的人们、所在的环境早已远去,昔时人们俯仰大地星空的感受却借由艺术而长存。龟兹、高昌、长安、洛阳等无数丝绸之路重镇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时光流逝,它们或毁于战争,或毁于风沙,或毁于时光,最终湮于大漠,埋于地下。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使一部分残影残像得以重见天日,残件的精美绝伦愈发引起人们的无尽想象与感慨。借助新的技术手段,人们也创造着艺术的古今穿梭。追往抚今,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唯有艺术因人而恒久存在。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馆长 李峰
Preface
Echoes of Camel Bells: Arts, Civilizations along the Silk Roads
The Silk Roads is a route for both trade and arts.
The multiple bustling routes of the Silk Roads connect the East and the West via land and sea, including the southern, middle, and northern lines. Dynamic to different extents in different eras, they had enjoyed their heydays respectively to facilitate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to exchange with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rts have spread, developed, and evolved along the Silk Roads in different ways, presenting a harmonious integration. Statue, mural, and calligraphy, which we consider as carriers of arts today, initially served to spread beliefs, decorate temples or tombs, and formulate legal documents. After thousands of years of vicissitudes, most of their original functions have faded away, leaving only the beauty of form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admire under the nam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ts.
Echoes of Camel Bells: Arts, Civilizations along the Silk Roads mainly includes five sections, namely “Preface”, “The Earth”, “The Mortal World”, “The Sky” and “Eternity of Art”. The exhibition mainly presents the rich artistic landscape of the eastern section of the overland Silk Roads, specifically, Luoyang, Chang'an, and Xinjiang in China. More than 500 pieces (sets) of exhibits that span 4,000 years and cover multiple categories such as painting, sculpture, statue, artifact, sound, image, multimedia, etc., jointly create a three-dimensional field, and display the diversity, resilience and vitality of arts along the Silk Roads. They quietly and constantly refresh their looks with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 Moreover, they have remained unfading over time and still inspire people today.
As time goes by, ancient people who created crafts and arts along the Silk Road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y lived in have long passed away. However, their feelings arising from observing the earth and the starry sky have been passed down to now through the arts. Countless strategic towns along the Silk Roads, such as Kucha, Gaochang, Chang’an, and Luoyang, had created brilliant art. As time went by, they were destroyed either by war or by wind and sand or by time, and ultimately buried in the desert. Since the 1920s, great archaeological efforts in China have unearthed some remnants, and the exquisite and unparalleled beauty of the relics has increasingly aroused people’s endless imagination and emotion. With the help of new techniques, people could trace the ancient arts. “Like a tiny drop of dew, or a bubble floating in a stream; Like a flash of lightning in a summer cloud; Or a flickering lamp, an illusion, a phantom, or a dream. So is all conditioned existence to be seen.” Art lives forever due to humans.
Director of Beijing Minsheng Art Museum Li Feng
策划打通古今——“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策展手记
李峰
2024年1月12日,展品时间跨度上下四千年的“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拉开帷幕。在长达半年的展期中,中、美、德、日、挪威等5国、14省市自治区、35座城市、从全球百余家各类型博物馆、大学、文博机构等遴选的500余组件雕塑、绘画、器物、丝织品、复制洞窟、多媒体装置等在6000余平方米的超大临时展厅展出。展览以开放的文化立场和当代艺术的策划手法来讲述文物故事,将艺术的美感与文物的历史感毫无违和地展示出来,从而开一时风气之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就其策展情况与各界方家汇报讨论。
突破创新与行业引领:驼铃声响大展的特色
一家美术馆的文化站位和艺术判断力是其灵魂。能否独立发起和策划实现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场艺术效果的展览项目,是判断一家美术馆能力最为核心的指标之一。带着如何将民生的文化公益事业更上层楼的任务,2020年6月我前往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主持工作。基于民生美术机构过去十余年的工作脉络,疫情正紧的当年9月,我们推出全球首个中国当代艺术常设展“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2020.9.5至今)。2011年10月,从“青春——安藤忠雄建筑展”(2021.10.12-2022.1.9)开始,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实现从完全免费到售票的转变,这家场馆从专注于当代艺术领域转向了更广的社会公众。
之后,从“五色斑斓——套色版画艺术四百年”(2021.1.28-4.30)开始探索,经“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2022.8.30-2023.5.5)拿出5000平米临时展厅超大规模进一步扩大尝试,在捐助人及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所提出的“将思想化为现场,将研究变成展览”“以当代的手法来策划古典艺术并打通古今,将艺术的美感与文物的历史感结合起来”这些理念逐次得以实现。其中,“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的策划无疑成为完整实践这一理念的最经典案例,在我看来,大展在三个方面拉开了同其他同类型展览的距离。
一、艺术之美的视角
丝绸之路展览无数,考古展、历史展、科技展、服装展、音乐展等等,各种类型丝绸之路专题展览不一而足。如何做出民生特色?毫无疑问,我们要做自己擅长的事,上述领域不是民生的所长,我也非此间专家。从艺术之美出发,这不仅无疑将调动起既往民生美术机构既往近20年的积淀,也展现出这家机构一如既往深耕耘于艺的坚定的姿态。实际上,即便单从艺术的角度切入也可谓浩若烟海。
如何实现突破创新?如何不再重复地堆砌文物、骆驼与丝绸?文博机构固然有其成法,但他们也想看到不一样的独出机杼。这不仅是极富难度的挑战,也是机遇所在。为此,在尊重学术的同时,必须破除对知识和学术的仰望和过度敬畏,必须大胆立意,勇于树新,必须删繁就简。我似懵懂但明确坚定的想法是聚焦于文物的艺术之美,回到儿童般的“纯真之眼”,回到人类最初的感觉与感知力。当然,关于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古今中外有无数解释。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希腊柏拉图说“美是理念”。它们概括而抽象,我无力也无欲拉玄奥之词以为大旗,但与其引用谁也看不懂的概念与说词,不如就回到人面对物的直觉感受。我们丝路大展策划的落地为不是考古,非同于历史展,不是文献堆砌,我们从大美不言的感觉与感知出发。德国哲学家鲍姆嘉腾1750年首次提出的“美学”Aesthetic实应翻译为感觉学,中国古人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丝绸之路历史太久,路线太过复杂且变动,非止一条,作品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展览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以文学的手法剪裁取意,如写小说般既有浓墨重彩处,也可大量留白,空白,穿梭跳跃,一如《百年孤独》并非拉丁美洲历史纪实,然而我们感受到那方遥远土地人们的喜怒哀乐,千百年来的坚韧魔幻。
带着这样的立意,我们出发调研。8个月间,仅我本人便前往35座城市、55城次、超过10万公里考察。在不断商谈借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序”、“大地”、“人间”、“天空”、“尾声”等5个篇章组成的展览主体框架架构。其中,“序”篇最为重要,它展现了民生的立场和态度——艺术的丝绸之路。在我们看来,丝绸之路不仅是“绘画之路”、“音乐之路”,它还是“玉石之路”、“小麦之路”、“纸之路”,它更是“丝绸之路”、“信仰之路”。在最终呈现的这一篇章的展览大厅,它们各自均有实物对应:
绘画之路/音乐之路: 吐鲁番阿斯塔纳230号墓出土唐《乐伎屏风绢画》;
黄金之路: 伊犁昭苏县北朝时间《镶红宝石黄金面具》;
纸之路/高科技之路/文明传播之路:北朝时期剪纸;
小麦之路/食物之路: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唐代小麦点心实物;
玉石之路: 和田地区出土玉石;
丧葬之路/民族融合之路: 河南龙门石窟唐代《石墓门》、《安思泰造像塔》;
雕塑之路/造像之路/信仰之路: 龙门石窟擂鼓台南洞初唐时期石刻《宝冠佛》;
丝绸之路: 青海吐蕃时期《红地团窠对鸟纹锦袍》;
9件作品置于空阔的大堂,疏朗概括。序厅的简括一举打破了丝绸之路线路过于繁多、文物过于庞杂对展览策划者带来的眼花缭乱,从而让工作易于入手,观众便于进入观赏状态。
“大地”、“人间”、“天空”是展览的主体部分,具体章节、展陈方式都进行了创新,策划团队甚至常常将整个篇章当作一件当代艺术展示。最典型的是“人间”部分的“百态人生”章节,25组展柜树林般聚于一厅,观众穿行其间如若游鱼,这是传统博物馆难以遇到的展出方式,观者得以多角度欣赏文物之美。著名的丝绸之路专家葛承雍教授在观展后说,山西博物院《黄釉胡人双狮纹扁壶》原来除了狮子之外还有大象!这件丝路艺术名作以前多只呈现正面,在我们的“游鱼”观展方式下,左右侧面巧构而成的两只大象才被看到。
至于“结语”,它是展览不可分割的“豹尾”——1500年前的世界最高建筑仅仅存在了18年,繁华一时间,但审美、人类的情感却因艺术而恒久存在。时间过去,生活依然要继续,艺术给我们以精神的愉悦、慰藉,它带来勇气、同情与爱。
我常常跟同事们讲起学者们发现的三重龙门的故事:
第一个龙门是宗教的龙门。1500年前北魏迁都洛阳开始开凿龙门石窟,那是佛教、政教合谋的龙门,这可以说是龙门石窟的“初心”与原始样貌。
第二个龙门是文人墨客的龙门。近1200年前,白居易写下“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自此吟咏传唱,开启了文人们的龙门。在所有的石窟寺中,龙门文人墨迹之丰富独一无二。
第三个龙门是艺术的龙门。1907年法国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前来龙门石窟,为其所震撼,他于1909年在巴黎发表《北中国考古图录》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Chine septentrionale,让世人从此看到一个纯粹艺术的龙门。
同样,丝绸之路即便“远看成岭侧成峰”,我们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切入,让它铅华洗尽。好展览在哪里都一样,它必须拥有好的品味,吸引人,让观者身心愉悦。吹去层层知识泥土与历史的尘埃,不分年龄、知识结构的男女老少观众可以直接领略丝绸之路艺术的生动鲜活。
于此之外,无数华丽珍宝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绿洲各自的产出无法满足独自生存与发展,交换成了存活的必须。在它们的背后,危机四伏,杀戮、抢劫、战争不断。好的展览必须有美的明星文物,但它又不是昂贵与珍罕的堆砌,以美串联展品的背后,是对人的同情,对天地的敬畏。在领略古今交通交流困顿、挣扎与美之创造的同时,展览最终所传达给观众的应该是平和的温暖,深切的同情,是无望绝望时的希望,是经人生冰冷与残酷之后的诚挚与爱。想法落地到现场是困难和挑战的所在,这一部分设想我们在展览的结尾部分得到较好的呈现。我们以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的两组装置《洛阳幻城》、《永宁绝响》来诉说物质的虚幻与短暂,以洛阳博物馆藏6件小而美、小而典雅的永宁寺造像来表达美借由艺术而长久存留,以庆城县博物馆藏21件国家一级文物、迄今古俑艺术水平最高的《穆泰墓彩俑》呈现时尚、幽默和乐观——不能沉浸于悲戚,生活是知其难后的依然充满希望,依然坚定的继续。《穆泰墓彩俑》旁边,展墙上挖出的长方形视窗往下回望,观众得以用近乎上帝的视角回望一楼序厅,俯瞰人间,于无言静默中重味展览。
走下三楼,到二楼我们又回到第三篇章“天空”的“行者圣人”部分。古代的法显、鸠摩罗什、玄奘,现代的常书鸿、韩乐然,一代一代的付出才有我们今天。再往前走,一件当代艺术家杨茂源的装置作品《曼陀罗·骆驼》引领观众走入美术馆的常设展厅。在这里,专门配合大展设立了“礼物”的篇章,丝绸之路非止于古于现代,它早在1000余年前已经创造了横跨不同区域的国际艺术,今天它依然鲜活,激励着艺术家的创造。
二、古今一体的展览结构
古代文物展品沉淀超过千年,厚重沧桑。现当代艺术虽时间不仅,展现出活力与富有思考的时代鲜活气息。打破古今的藩篱、展现今天的文化自信创造并非一时冲动,早在20余年前大学读书时我便曾朦胧有此想法,并试图在2010年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开幕展“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历程(绘画):1979-2009”尝试而未得。
2021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书店等机构和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学院等版画相关专家及各界藏家的支持下,“五色斑斓——套色版画艺术四百年”首次进行了跨越古今的尝试。套色木刻水印艺术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让我们在这一领域至今享有较高地位,当代则展现了艺术家们不拘于技术语言、深入今天社会生活的能量。两年前我们初试啼声,一举破除了两个圈层的相对封闭——古籍圈看到丰富新奇与当代大尺幅版画的视觉震撼,当代艺术圈则领略到技术的厚度与精雅。“文明的印记——敦煌艺术大展”首次系统性地、大规模地将古典艺术、现当代艺术混合展出,巨大体量的佛像、大小不一的8座洞窟有如装置般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和带入感,它们与现今流行的当代艺术双年展的感受并无本质区别,然而时代更久远,受众更广泛。现当代艺术方面,常书鸿、董希文等值守大漠时的创作型作品让观众看到人间之人,人的外观,人的所行所居,生产劳作与精神面貌。今天艺术家创作,更是突破地域和时代,力图展现出人与环境的冲突与共存,艺术家们超前思索着人的尊严与未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没有前几个烧饼就没有吃到第六个时的肚饱。“驼铃声响:丝绸之路大展”在古今结合上的学术深挖与独立果敢,经过两次大胆尝试之后水到渠成。驼铃大展的主体部分基本全部为古代文物或文物的临摹品、复制洞窟,至“天空”版块的最后一个章节“行者圣人”将古今结合起来。这部分首先呈现的是鸠摩罗什、玄奘等历史上的学术大师对文化艺术和人类文明融合的卓绝贡献。继之,是以常书鸿、韩乐然、袁运生等为代表的现代艺术家对古代艺术宝库的保护、对今天艺术的创造与推动作用。紧接着,便来到我馆常设展“绵延:变动中的中国艺术”的丝绸之路艺术大展特别篇章“礼物”,刘小东、段建宇、王兴伟、旦儿、马轲等艺术家以其或写实或意向的风格,调动油画、影像、行为、装置等多种手法,给古老以回应——今天丝绸之路依然生机勃勃。不仅如此,我们还将一些以新手法表现古代题材的作品纳入展览,如1927年的黑白无声电影《盘丝洞》、动画电影《鸠摩罗什》等。
独特的展览结构以事实告诉各界民生美术馆不会仅做优质展品的巡展场地,它有着自身的文化判断与立场,我们对本馆的学术判断力与敏感度抱有极大信心,我们相信这样的创新经得住时间考验。
三、尽量去除展品与人的中间环节
建立展品和人的直接交流对话,在丝路大展策划团队看来是美术馆的核心优势之一。从展品选择到现场呈现策划,我们均有意识地尽可能不去掉书袋,不去过多地引用行业专家意见。清除掉过多的作品阐释和言说,从而让观众能够更为聚焦于艺术作品本身,直接体验展品的艺术之美。
展览现场尽可能裸展,尽可能不要过多炫目的声光电干扰,去掉不需要的玻璃展柜,尽可能地减少众多展览拥堵一起的大通柜。为给作品以充分的空间,策划团队制造出多处展品在所在第地都没有的空间距离与环境场景。这其中以龙门石窟《宝冠佛》、青州隆兴寺造像、夏琼寺《时轮坛城沙画》、柏孜克里克第15窟复制等最为典型。如若全然重复《宝冠佛》所在的东山擂鼓台南洞,于时间上来说扫描与制作都很紧迫,更重要的是它比不了空旷的场景与12米高、裂中缝背屏肃穆而时尚的视觉效果和现场体验。对于青州隆兴寺造像群来说,暗下来的光让造像更突出,它们每一尊佛像与展台、背屏、作品前的玻璃一起组合起来犹如装置,而所有的“装置”又共同组成一组更大的装置。《坛城沙画》由青海而来的5位喇嘛耗时7天完成。展品基于宗教的信仰,却又在美术馆的展厅脱离了宗教的语境,观众看到的是华美繁复的沙画、制作的细致精良,感受到作品背后信仰的博大宏阔。它们基于实物,基于千百年的岁月积淀,作品自身之美让其内在生光,这远非一些展览体制内兜兜转转的寻常“当代艺术”外在的赋予意义与硬性加入的空洞形式所能比拟。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然而作品就在那里,千百年不因外在而改变。美术馆就是要清除令人目盲的五色,令人耳聋的五音,尽可能地让现场干净,让作品独立,互不干扰。我们最大限度缩短作品与人之间的距离,释放作品的开放性,让观众各自感受。
“活”而非静止不可讨论的展览
文物展品之上的宗教礼拜、丧葬礼仪等实用功用,历代知识的叠加与赋予等等,早已随着使用环境的改变而被剥离,远离。没有人的介入,古寺空壳,艺术只是标本。因为人的到来,丝绸之路作为一个集大漠雪山、建筑、壁画、雕塑等为一身的变动艺术综合体,重又“活”起来。是人策划,人的的欣赏、研究和创作让它重又有了生命的灵动。一代一代的“当代”叠加,让丝绸之路一代又一代沉淀出厚重,活力出新生。
来到现场的观众们发现很多“驼铃声响:敦煌艺术大展”的与众不同之处。这观众既包括专业的学者、策展人、美术史家,更包括更多的观赏者、游玩者。起初,志愿者们疑惑讲解不知如何下手。既往按照时间、区域展开、穿插故事的套路不再那么顺手和奏效。与此同时,观众们却体会到一种乐趣,即便也有茫然,但不复知识说教的扑面而来,展览能够轻松地进入——无论从哪个篇章、哪件作品开始,都能够愉悦地感受到丝绸之路艺术的丰富华美、新奇神秘。整个展览看下来又觉得充实沉重,收获满满,他/她不再是被动地被灌输,而是主动的感知、抓取与寻觅。
某种意义上说,让博物馆、美术馆的作品“活”起来远比如何搜集、聚拢、整理更为重要,即便这些收藏工作是“活”起来的前提。通常来说“标本”活起来的前提在于:
一、对物理事实的考据与认定。
文物证实历史的功能让无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为发现哪怕只有只字片文的遗存而激动不已。事实上,文字的发现也确实是让文物活起来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有无数的例证让文物找到其所属,它的年代,它的主人,它的功用。有铭文的器物其价值远远高于无文字者,这早已成为业内定论。同样,一幅流传有序的画作,历代题跋让其声名显赫。一件密密麻麻题满文字的碑帖价值甚至可以远远胜过原碑原石。
文字是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对文字的认定与研究却不是美术馆的天然工作,术业有专攻,它理应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美术史家们来完成。没有考古队的前期挖掘、整理和考古报告为基础,后期博物馆工作很难推进。专家们完成文物在历史上的归位——它们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在什么场景之下、谁有资格来使用,等等。专家们解决“标本”与时代的关系。
二、风格变迁的归纳梳理。
对于“标准”风格的变迁梳理往往是由考古学家和美术史家们来完成。其内在的学术支撑对于考古学家们来说是类型学和地层学,对于美术史家们往往是图像志的建立与分析。
以上两项前提,无数博物馆、研究机构、专家进行了上百年的工作,“驼铃声响——丝绸之路艺术大展”可以说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将思想、学术研究化为现场,我们的突破口是艺术、审美,是人类最原初的感觉感知。一个懵懂的儿童不知道到什么是文字,什么是知识,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故事,但他/她看到图像会有感知。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岁余的孩子听到音乐声翩然起舞,但他/她并不知道什么是音符和旋律,什么是音乐。事实上也无需知道。
以艺术和审美切入,以人的感觉感知力为切入口,让美术馆获得一方独特的天地。在这里,美术馆人得以自由驰骋。由此,我们来到了美术馆工作可能的核心所在——呈现物与人的关系、讨论物与人的没有边际限制的可能性。这里的物,毫无疑问不再是考古之物,它是作为人的感觉寄托所在的“艺术”。由于可以进行讨论,很多时候作为考古遗迹存在功用不明的物品,在美术馆也天然获得了它的自由度,其使用目的、仪式场景等等均可以讨论,可以争议,可以想象。
如果说“序”体现我们策划展览的态度、立场与初心的话,那么“大地”、“人间”、“天空”三个篇章可以说展现的是大展的主体内容与民生的分类方法。“大地”由“先民之土”、“丝”、“行路难”三个章节组成,讲述公元前138年张骞通西域前后东西方的生活、对彼此的想象、往来交通。“人间”分为“胡容汉貌”、“百态人生”、“万里同文”、“古乐今声”等四个章节来呈现异彩纷呈、悲喜交融的丝路人间生活。“天空”部分讨论信仰传播、佛教艺术的变迁等,分为“多元信仰”、“佛艺东渐”、“化梵为夏”、“行者圣人”四个部分。所有的这些篇章均以绘画、雕塑、复制洞窟、书法等方式呈现,无不紧紧围绕艺术、人的审美与感觉为中心。
美术馆不是考据之所、说教之场,而是依仗感觉与审美启发想象力的园地。
策展是遗憾的艺术
几乎所有的展览所呈现的均是结果,一如我们去餐厅就餐,多半不会看到厨师的背景、原料的采买、烹调的过程,至于如何摆盘、空间如何设计等等前端显然也较少受到关注。结果掩盖了大量的生动过程,人们也看不到其间的错误,失误,遗憾以及不测的变故与逢凶化吉,山穷水尽疑无路后的柳暗花明,坏事变好事的意外之喜。就此展览,我们所遇遗憾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
一、速度与效益的矛盾
不止一位朋友问起我:这个展览准备多久?大展合作伙伴之一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的负责人说,在美国减一半文物、一半展览面积需要至少7年。国内文博机构做此类展览一半需要3-5年。我们固然以创纪录的民生速度用不到11个月做出如此规模大展,但显然一时突击可以,长期不可持续,展览有其内在规律。
二、展览大纲的确定性与展品的不确定性
文物展最核心的部分是展览大纲,它是展览得以成立、得以推进的关键,往往由相关领域专家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各机构商谈的根本依据是展览大纲,出借机构最希望的是看到完整确定的展览大纲,从而方便开展工作。没有锐意创新的策划和完备的展览大纲,即便均是国宝名作,展览也因散珠不成串而无法成立。但反过来,名作很忙,档期难凑,这让展览大纲难以确定,动态调整中,最终的展览面貌和最初的设想往往差异极大。
三、感知与知识的矛盾
以艺术之美为出发点的展览,往往希望抛弃既往满天满地密布的各种展品说明、解释,各类型图示图表,各种辅助说明照片,它们琳琅满目将主要作品淹没其中,将展览变成杂货铺般的堆积。因为建馆时间久,作品收藏日多,这对很多国际最为知名的博物馆也无法避免。然而我们精心设计的空无杂物的现场空间也往往引起一些看惯解释说明观众的投诉,即便二维码扫描在旁,即便移动搜索至为方便,很多人依然依赖于积习。
四、创新与抵触
很多展览专家明确说,我们办展只办我们相关的展览,不希望掺杂现当代等其他内容,似乎它们打乱了既有的节奏。稳妥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但出彩一定要有大胆锐意进取,新策划、设计、展陈的理念跨界使用,才能创造出奇制胜。当然,创新是基于对既有展览套路的熟知和对新鲜手段的合理利用。
遗憾当然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具体的案例不胜枚举,几乎每个展览都有多个。敦煌大展将285窟抬高至4米空中的想法实施至一半,我登上疫情中一盼再盼才从河北运来的脚手架,晃动!拆除有时间,再搭建的风险已然承受不了再不行的拖延,开幕在即,为了施工的安全,只好连夜取消。驼铃声响大展,黑川良一声音装置给整个展览以颠覆性的更新与提升,考虑到空间的分布与公众可能的误解——他的作品跟丝绸之路什么关系?也在临近落地的时候取消。此外,洛阳古墓博物馆《安国相王孺人墓胡人牵驼》壁画的擦肩而过,也让人怀想无比。
作为开放学园的美术馆
展览策划与实施的过程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长期以来我所从事的美术馆工作。如所周知,英文中美术馆和博物馆是一个词,在中国二者之间区分较大。一般来讲博物馆更古,展示和保管的条件要求更高,美术馆的工作对象则相对年轻,和时代贴的也更近,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和探索性,更为活跃,更能容错。过去几年我们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博物馆、美术馆之间的泾渭分明,实际上,一些同行也在尝试实现二者的融通与“跨界”。那么,我们不禁要追根溯源,作为人类文明保存、研究与欣赏的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什么是博物馆/美术馆?它能做什么?
距今约2300余年前,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创建者托勒密一世兴建“缪斯神庙”(mouseion,希腊文)献给文艺女神缪斯。它因贡献了museum一词,而曾被一些专家视为今天博物馆的起源之一。但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美术馆及其运营机制的建立不足250年——一般将1793年8月10日卢浮宫对公众开放这一事件视为现代意义上公共艺术博物馆建立的标志。换言之,如今我们所习惯的出国和外地旅游探访游览博物馆之举不过230年余的时间。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形成还要更晚,以公认的中国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建立的1905年算起,不过119年。
1946年11月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useum,ICOM)自成立之日起,到1951年、1962年、1971年、1974年、2007年、2022年,分别多次对博物馆定义进行了讨论和修订。最新的表述于2022年8月24日在布拉格举行的第26届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通过,决议将博物馆的定义表述为“博物馆是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常设机构,它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有可及性和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进行运营和交流,并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在中国,最新的表述出于2015 年国务院颁布《博物馆条例》:“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营利组织。”
美术博物馆与自然科学博物馆、应用科学博物馆、技术博物馆的差异巨大,但与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的边界日渐模糊。究其根本,原因或在于进入博物馆的藏品业已失掉原有的功能、存在语境等,历史价值逐渐退让给美学价值。在中国,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大部分最有影响力的省、市、县博物馆大量收藏、展出的作品是艺术品。“博物馆界”和“美术馆界”人士自认的区别往往在于年代,博物馆收藏和展示的作品更古,美术馆多是现当代。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中国博物馆和美术馆两者没有本质区别。不止一位文博系统的领导和从业者跟我说过博物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全国博物馆是一家。
短短的230余年时间,人类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艺术博物馆的庞大世界。无数或体量巨大或轻妙细微的物品以文物或艺术品的名义聚拢到美术馆的屋檐之下,它是文化的殿堂。“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民生美术机构体系于近20年前的2005年左右进入艺术公益,最初是捐助支持学术展览活动。2007年至2013年,我们接受委托管理运营1949年之后的第一家民营博物馆炎黄艺术馆,2010年民生第一家独立捐助运营的场馆开张。2020年起,民生系列美术机构以“四个服务”的定位实现全面升级:
服务国家文化战略
服务社会公众
服务民生银行的社会责任事业
服务民生银行品牌的塑造和主营业务的开展
结合捐助人的“四个服务”,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大跨步地实现了由专业的当代艺术馆向跨越古今、面向更广大社会受众的转身。基于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的百年经验,民生美术馆愿与国际同仁一道:
“鼓励公众通过探究藏品获得启迪、知识和快乐;……研究、共享和阐释相关文物藏品的信息,并反映不同观点。”(英国博物馆协会)
“博物馆以服务公众知识、教育和欣赏为目的而组织藏品,代表公共利益保护和陈列藏品的永久性机构。……为知识的进步、研究以及传播而贡献力量。”(法国博物馆协会)
博物馆/美术馆既是面对人类历史、文化与记忆的储藏间,更是奔向未来的想象力实验室。一家年轻的博物馆这样的自觉意识、文化立场与站位,它无疑有着随时刷新自我、沟通公众、打破壁垒的功能。美术馆又是由一个又一个展览组成,系统、有着知识和审美关联的展览往往创造出胜过单件艺术名品的价值。一个好的展览显然也不应该是简单的宝物堆砌,不是知识的堆垒与炫耀,不是再造光影的表面炫目。它不出虚张声势的面孔,不做作,不伪装,无形带入观众走进,无声对话,带来生命的启迪。对于学者们来说,可以进行学术的讨论。对于公众来说,能够真切体悟到我们先人生活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凭物以见人,观众看到一代一代先人的目光所及,头脑所思,心灵所感悟。
为此,我们主张,在文博行业专家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之上,把研究化为立体的现场,努力建设艺术公益的宏伟之业:
这里更为鲜活地展现教育公平与知识共享;
这里越来越成为一堂生动的开放大学的开放课堂;
这里让年轻人的青春热力四射,让已至中年或已白发苍苍人生获得喘息与反思;
这里让奋斗者休息,让疲劳者放空,让忧虑者放空和冥想;
这里的梦想更为无拘;
这里思想更为自由,翱翔于九天,搏击于四海;
这里得以更为单纯宁静地欣赏艺术之美;
这里激发当下想象力,鼓动起悄然蓄力的面对未来的创造;
……
很多年来博物馆曾被人们认定为垂垂老矣之所,显然这并非事实的所在,我们不能以博物馆内上下数千年的藏品来论断博物馆本身的年龄。即便放到缩短了的、有文字记录的人类历史长河,博物馆它也依然无比年轻。非止于企业社会责任担当与百年老店长远品牌塑造的助力平台,美术馆是艺术与生活的交界地,是生命尊严生活的地方,这是我们努力促成创新展览的初心所在。
编辑人:翟若冰